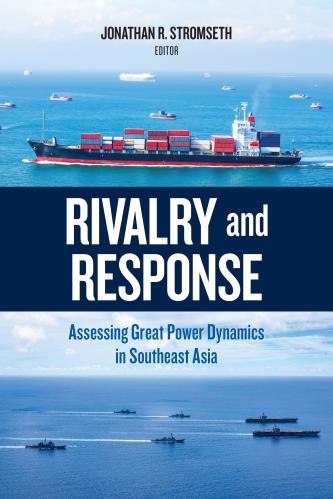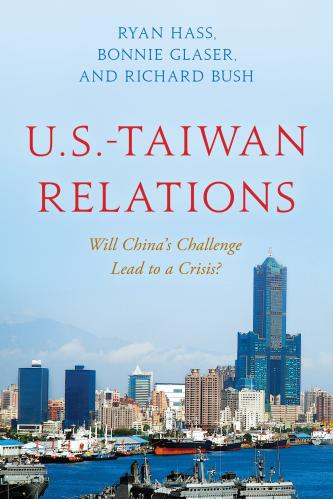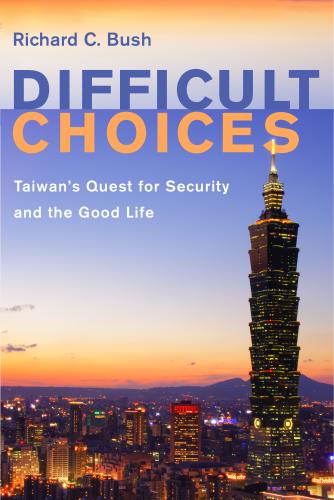Content from the Brookings-Tsinghua Public Policy Center is now archived. Since October 1, 2020, Brookings has maintained a limited partnership with Tsinghua University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that is intended to facilitate jointly organized dialogues, meetings, and/or events.
广袤的南中国海(South China Sea,以下简称“南海”)如今已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热点之一。包括中国在内的六个声索方都在借助言辞与行动,争取其中大量小型地物及富含资源海域的控制权,而美国亦因盟国及自身安全与经济利益而深度涉及其中。我们的时代所需回答的重大地缘政治问题,即当下拥有支配性地位的超级大国美国究竟能否与复兴中的强大中国和平共处,正如一只巨大的“柴郡猫”(Cheshire Cat)端坐在海平面之上,阴魂不散地冲我们咧嘴怪笑着(英国作家路易斯·卡罗尔在《爱丽丝梦游仙境》中创作的形象)。
多数当事方近年来都颇为冒进,但中国在对南海海洋地物与水域提出广泛的主权诉求上尤为大胆。其同时也大胆地在海洋地物上填海造陆,使权利主张转变为物理性建筑,并威胁将进一步军事化。中方迅速扩张的海军活动范围及战斗能力,增加了周边较弱邻国与美国的顾虑,而正是后者的驻军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极大地促成了亚太区域的和平与稳定。意外事件或小型冲突导致危险升级的风险是常在的。目前,仍没有一条解决大量争议并控制其带来严重风险的路径,但美国已经阐明了一种方案,阐明其不会就相互竞争的主权主张选边站,而是呼吁各国诉诸基于法律(law-based)、基于规则(rule-based)的途径来解决争议。正如奥巴马总统近日所言,美国所致力实现的区域秩序中,“国际规则与国际规范需要得到遵守,国家无论大小,其权利需要获得保障。区域内的主权争议必须通过法律途径和平地解决,如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即将做出的仲裁裁决,各方均有义务尊重并遵守。”[1]
上述声明体现了奥巴马总统外交政策的一个标志性理念:国际争议应当以基于法律的方式、经由法治过程来解决。本文所希望阐明的观点既简单但也略带遗憾:理论上,在国际舞台诉诸基于规则与法律的途径来化解争端实属难能可贵,然而法律并不能从根本解决危险重重的南海问题。更具体而言,即将到来的、基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中菲仲裁案实体问题裁决无法解决上述难题,甚至可能难以在这方面带来任何重大进展。
一、背景
南海是一片覆盖了140万平方英里的巨大海域,沿海诸国则容纳了将近20亿人口。全球约三分之一的海运都途径这里,此海域还提供了大量食物资源,其海床蕴藏丰富的油气资源。海域中散布着大量小型海洋地物,它们往往规模微小且多在涨潮时被海面没过。这些地物可以被归入两大岛群,北部的帕拉塞尔群岛(即“西沙群岛”)以及南部的斯普拉特利群岛(即“南沙群岛”)。中国、台湾、菲律宾、越南、文莱与马来西亚各方均对上述区域内的部分地物与水域主张主权,这些诉求之间存在冲突。中国则基于其“九段线”地图及诸多宣言,主张其对南海内全部岛屿、岩礁的主权及对毗连水域的权利。除中国外的其它五个利益攸关者彼此间也存在相互冲突的权利主张,而这又进一步增加了大量相互重叠且冲突的关于临近海域归属及其如何使用的主张。无论是海域的宽广抑或是争议地物的微小都未能阻止冲突强度于近几年层层升级。上述紧张局势多是受到了安全及资源考量的驱动,而各国彼此敌视的民族主义情绪则又为这片紧张的海域火上浇油。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国际条约之一,其序言以这样一段豪言壮语作为开场:“(本公约缔约各国)本着以互相谅解和合作的精神解决与海洋法有关的一切问题的愿望,并且认识到本公约对于维护和平、正义和全世界人民的进步做出重要贡献的历史意义”。有别于其他许多伟大事业,这一宣言并不是唱高调,而更多是以略显冗长的文字去表达人类对于“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思虑。
《公约》中除提供实体规则之外,还包括了可由成员国发起、用以追究其他成员国违反《公约》规则的救济机制。菲律宾和中国,以及世界上其他164个国家均加入了《公约》,而美国则属于少数没有加入《公约》的国家之一。2013年,菲律宾援引《公约》救济条款,在荷兰海牙常设仲裁法庭针对中国提出共15项仲裁请求。这正是前文中奥巴马总统所提及的案件。中国立即表达了其对菲律宾行动的“坚决反对”,呼吁菲律宾“回到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南海有关争端的正确道路上来”,并声明“中方不接受、不参与仲裁的立场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2]中方固然坚守了这一誓言,尽管其于2014年12月7日所发布的一份详尽的《立场文件》连同其他声明,都在实际意义上起了送达文件、参与诉讼的作用。[3]
此案所提出的一个先决问题在于,基于《公约》所设立的仲裁庭能否对这15项仲裁请求行使管辖权。“管辖权”系一项法律概念,用以反映法庭针对某一争讼中实体问题做出裁断的权力,而管辖权问题又区别于法庭在确立管辖权后如何决定案件实体问题中的“是非曲直”(merits)。
2015年10月29日,仲裁庭公布了广受误解的、总计151页的管辖权裁定书。仲裁庭确定自己就菲律宾所提请求拥有管辖权,但仅包括其中7项请求。仲裁庭未确定对另外8项请求的管辖,其中包括要求判定中方著名的“九段线”主张违反《公约》的请求。针对这8项请求,仲裁庭决定推迟管辖权裁定,原因在于这部分请求的管辖权问题与实体问题密切纠缠,故须等到其决定实体问题时再一并判断。
中国方面立即声明抨击该管辖权裁定是“无效的”且“对中方没有拘束力”,并谴责仲裁庭“滥用程序……严重侵犯中国作为《公约》缔约国的合法权利”,“损害了《公约》的完整性和权威性”[4]。该声明称菲律宾发起仲裁的行为构成了“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挑衅”,并呼吁菲律宾“通过谈判和协商”与中国共同解决南海有关争端。[5]
仲裁庭于2015年11月的四天内听取了实体问题的口头答辩。口头答辩过程中并无中方代表参与或出席。人们期待已久的实体裁决预计将于2016年5月或6月问世。各国如今需要深思熟虑应当如何回应,尽管大家此时只能就仲裁庭究竟会做出何种判定进行推测——只有少部分人熟知相关法律从而能正确理解仲裁庭的裁决,而能理解这一裁决的重要性及其将如何影响未来解决南海危机的路径的人则更是凤毛麟角。
二、仲裁庭裁决的限度
不难理解的是,奥巴马总统及许多其他人都对仲裁庭裁决为南海最具争议的问题提供法律解决方案寄予希望。法治手段是和平的,它承诺公正且无偏地适用规则,并会同时保障弱者及强者的利益。此外,通过适用法律,法庭也可以为因政治僵局而无法获解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然而,对呈递至仲裁庭的争议以及仲裁庭所可能给出的最终裁定的分析,表明仲裁庭与法律仅能够为南海危机的解决提供极其有限的贡献。法律无法使我们从对谈判和权力政治继续倚重中解脱出来。仲裁庭的裁决并不会成为各方未来沟通博弈中的主要支点,未来的进程需要我们更加着力于那些仲裁庭必然无力触及的问题,并尽快借助其他途径来处理这些问题。以下是我认为仲裁庭只能带来有限贡献的四个基本原因:
1.尽管有关媒体报道中存在诸多混淆之处,但它们无不承认仲裁庭无权对就南海岛屿和岩礁的“主权”归属问题做出任何裁定,尽管此类“主权”问题才是当下诸多争议的核心。
2.各方无不承认,中国有法律上的权利根据《公约》第298条,在批准条约后声明排除强制性争端解决程序对包括“海洋划界”(即厘清不同国家间相互重叠的海洋权利主张) 、“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或“军事活动”等一系列争议问题的适用,故仲裁庭也就不会对任何此类争议做出裁断。
3.假设仲裁庭会在裁断提交的法律问题之过程中公正严明(我们自当如此假设),则菲方针对中国的15项仲裁请求不大可能全部获得支持。仲裁庭有可能裁定其对菲方提出的部分请求缺乏管辖权,并否决掉菲方的另一些请求。
4.即使菲方所提的15项请求部分甚至全部为仲裁庭所支持,即使这一对中方不利的裁决将能够对中国产生“拘束力”,现实中依旧不存在任何强制执行机制。中方以管辖权为由拒绝参与仲裁程序早已预示了任何不利于中方的裁决将有的结果。
证立上述结论需要我们投身于如水草般纷繁复杂的法律细节之中,去逐一分析菲律宾所提出的法律诉求。而这些“水草”正是法律的领域,也正是法律解决方案通常倚赖的基石。外交政策专家不能只是呼吁用法律途径来解决国际争端,而丝毫不直面实现该途径所需的投入,以及法律途径究竟所能或者所不能提供的结果。
三、法律与海洋
菲律宾针对中国共提出15项仲裁请求,[6]本文概括如下:
(1) 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不能超出《公约》允许的范围;
(2) 中国主张的对“九段线”范围内的南海海域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以及“历史性权利”,与《公约》相违背;
(3) “斯卡伯勒礁”(黄岩岛)不能产生专属经济区或者大陆架;
(4) 美济礁、仁爱礁和渚碧礁均为低潮高地,因而不能成为取得主权的对象;
(5) 美济礁和仁爱礁为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一部分;
(6) 南薰礁和西门礁均为低潮高地,不能产生领海、专属经济区或者大陆架,但可能被用于测量领海宽度基线;
(7) 赤瓜礁、华阳礁和永暑礁不能产生专属经济区或者大陆架;
(8) 中国非法地干扰了菲律宾享有和行使对其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生物和非生物资源的主权权利;
(9) 中国未能阻止其国民和船只开发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的生物资源;
(10) 通过干扰其在黄岩岛的传统渔业活动,中国非法地阻止了菲律宾渔民寻求生计;
(11) 中国在黄岩岛和仁爱礁违反了《公约》下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义务;
(12) 中国对美济礁的占领和建造活动, 违反了《公约》关于人工岛屿的规定及中国在《公约》下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义务,并且是为试图将该地物据为己有的违法行为。
(13) 中国危险地操作其执法船只给在黄岩岛附近航行的菲律宾船只造成严重碰撞危险的行为违反了其在《公约》下的义务;
(14) 自从2013年1月仲裁开始,中国非法地加剧并扩大了争端,包括干扰菲律宾在仁爱礁海域及其附近海域的航行权利、阻止菲律宾在仁爱礁驻扎人员的轮换和补充,并危害菲律宾在仁爱礁驻扎人员的健康和福利;
(15) 中国应当停止进一步的违法权利主张和活动。
菲方的仲裁请求均已经过精细的雕琢,试图规避业已限定整个仲裁程序并凸显仲裁裁决将非常受限的两大障碍。首先,无可置辩的是仲裁庭无权就任何牵涉岛屿或岩礁的“主权”归属争议做出裁定,尽管各国间相互冲突的“主权”主张正是南海争端的主要动因。菲方律师都心知肚明,《公约》并不处理主权问题,此次的仲裁庭同样也会避开主权问题。海牙国际法院(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可以就“主权”争端做出裁决,但必须以争讼各方同意为前提——毕竟,国家同意是多数国际法规范的基础。囿于南海争议中的各方均不会都同意仲裁,作为南海问题核心的诸多“主权”争议获得仲裁解决将遥遥无期。
其次,《公约》本身也允许签署国自行排除强制性程序针对《公约》所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适用。《公约》第十五部分针对导致有拘束力裁判的“强制性程序”作了明确且至关重要的规定,但该部分也明确包括了若干例外条款,并且已被中国所主张。(译者注:《公约》第二百八十一条第一款:“作为有关本公约的解释或适用的争端各方的缔约各国,如已协议用自行选择的和平方法来谋求解决争端,则只有在诉诸这种方法而仍未得到解决以及争端各方间的协议并不排除任何其他程序的情形下,才适用本部分所规定的程序。”)首先,《公约》第281条排除了强制性程序对争议双方“已协议用自行选择的和平方法来谋求解决争端”的情形。但中方所援引的有关中菲间协议仅仅是模糊的政治性声明(译者注:此处应该是指《中国政府关于菲律宾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中援引的2002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菲律宾共和国联合声明》),故无法被合理地视为具有排除《公约》强制性程序的效力。仲裁庭也已经驳回了中方对此例外的援引,如此认定也应被认为是妥当的。
不过,《公约》第298条也允许成员国自行将其他争议作为例外而排除出强制性程序适用的范围,而中国及其他国家均已采取必要手段去创设相关的例外,进而限制仲裁庭所能处理争议的范围。第298条特别阐明成员国可以“用书面声明对于下列各类争端……不接受第二节规定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程序”,其中包括“关于海洋划界的第十五条、第七十四条和第八十三条在解释或适用上的争端,或涉及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的争端”、“关于军事活动……法律执行活动的争端”。中国已通过书面形式宣布不接受《公约》强制性程序针对上述类别争端的适用。
这里所排除的争端范围的确颇为广泛。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也许正是排除涉及“海洋划界”的争端。这类争端主要发生在各国就《公约》规定的岛屿或岩礁所产生的12海里领海或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提出重叠主张之时。“海洋划界”则是一种为重叠主张确定边界的方法。由于针对南海中岛屿与岩礁的主权争议如此之多,而其中这些海洋地物间的距离又常常不超过200海里(有时距离甚至小于12海里),主张重叠的情况普遍存在。正如下文就菲方具体请求的分析所显示的那样,将“海洋划界”排除出仲裁庭管辖权范围将极大地限缩其裁决。下文也将展示,排除“海洋划界”、“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军事活动”或“执法活动”相关争议的仲裁管辖权,至少会给仲裁庭带来必须首先克服才能进一步处理其他重要问题的困难。
简言之,此次中菲仲裁案中仲裁庭事实上无法就任何涉及主权归属、“海洋划界”、“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军事活动”或“执法活动”的问题进行裁定。这使得仲裁庭的管辖权极其有限。它被禁止就中菲两国在南海的大部分主要争端进行裁决。这也意味着仲裁庭将无法为解决这些争端提供“基于法律”的答案。我们唯有具体考察菲方在仲裁庭前实际提出的诉求,方能明白上述结论的涵义——我们要穿越这杂草丛生的法律领域。
让我们首先分析仲裁庭已经宣布具有管辖权的7项菲方仲裁请求。这一管辖权裁定无疑是有利于菲律宾而不利于中国的。这其中包括了前述的第3项、第4项、第11项及第13项仲裁请求。其中又有4项请求(分别是第3项、第4项、第6项与第7项)寻求仲裁庭界定特定的海洋地物,裁断这些地物应被归入《公约》所规定的哪种具有法律意义的范畴之中——“低潮高地”、“岩礁”抑或“岛屿”。仲裁庭关于海洋地物归类的裁决将十分关键,因为这会成为更具争议的、仲裁庭无法触及的主权和海洋划界问题的基础。归类决定同时又会牵连到仲裁庭所需处理的其他问题,如中国在此类地物周边活动的合法性。
假设仲裁庭将某一海洋地物仅界定为一块“低潮高地”,则任何国家都不得对之主张主权,除非该地物确实处在该国领海之内。如果仲裁庭宣布该地块属于一个“岛屿”或是“岩礁”,则会带来以下几种后果:
(1)国家可以宣布这些岛屿与岩礁为本国的领土(尽管仲裁庭并不会在此处判定应由哪个国家对之享有主权)。
(2)如果该地物被判定为是岛屿,则对其拥有主权的国家可同时取得12海里的领海、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以及相应的大陆架。
(3)倘若该地物被判定为是岩礁而非岛屿,则对其拥有主权的国家只能连带拥有12海里的领海,而不包括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
(4)倘若另一国拥有对附近“岩礁”或“岛屿”的主权,则上述结论将会受到限制。各种原因在于两国间的领海及专属经济区将会发生重叠,因而必须进行海洋划界。考虑到各方皆认可中国可以基于《公约》第298条排除《公约》所确立的强制争端解决机制,仲裁庭不得在本案中做出涉及海洋划界的裁断。仲裁庭在其早前关于确立对第4、6项仲裁请求管辖权的裁定中,加入了一条重要的“有关任何权利重叠之可能影响的特别声明(caveat)”。[7]
仲裁庭可能会认同菲律宾在第3项、第4项、第6项及第7项中针对不同地物的归类。实际上,并不清楚中国就菲律宾所提出的归类方案是否持有任何异议。仲裁庭很可能会判定“斯卡伯勒礁”(“黄岩岛”)属于“岩礁”(第3项请求);美济礁、仁爱礁和渚碧礁均为“低潮高地”(第4项请求);南薰礁和西门礁均为“低潮高地”(第6项请求),而赤瓜礁、华阳礁与永暑礁均为“岩礁”(第7项请求)。
针对这四项请求所作出的裁断并不会直接宣告中方的行动为非法。对地物的归类将会影响到任意一个对特定“岩礁”或水域拥有主权的国家所能享有的附带权利,但仲裁庭并不会直接判断究竟是哪个国家对此地物拥有主权。就算是判定某一处在领海以外的海洋地物属于“低潮高地”,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对之主张主权,这一裁决也不必然会阻止中国或其他国家在此低潮高地周边建造人工岛。尽管人工设施不会改变低潮高地的性质并使之转化为可被主张主权的“岛屿”或是“岩礁”,这仍不意味着中国就被禁止围绕低潮高地或在其上开展填海造陆工程。这是菲律宾在其另一个请求中所提出的另一个问题,而仲裁庭尚未宣布它是否要就此问题行使管辖。
仲裁庭已经宣布将要行使管辖的另外三项请求(分别是第10项、第11项和第13项请求)则旨在挑战中国在南海两个特定地点——分别是“斯卡伯勒礁”(黄岩岛)、“第二托马斯礁”(仁爱礁)——附近国家实践的合法性。以上请求十分重要,其直接挑战中国正在进行的一系列特定活动,尤其是在如今变得有名的黄岩岛附近的活动(译者注:即自2012年起中菲两国政府船舶在黄岩岛附域海域的公开对峙)。针对上述请求的裁决有可能会激起中菲两方的激烈反应,但事实上上述请求仍然未能深入到南海争端的核心,即主权与海洋划界问题。
第10项请求声称中国阻碍了菲律宾渔民在“斯卡伯勒礁”(仁爱礁)附近的捕鱼活动,而仲裁庭有可能会在裁定第3项请求时将该地物界定为岩礁。中菲两国皆主张对该地物的主权(菲律宾同时还认为该岩礁处在由本国海岸所生成的专属经济区内)。然而囿于仲裁庭无权就主权归属做出裁定,出于要分析菲律宾在中国领海以内捕鱼权利的考虑,仲裁庭又还必须假设中国对该地物享有主权。这将极大地使菲方关于中方干扰其国民捕鱼权利的指控复杂化。通常而言,一国国民无权在他国领海内捕鱼——领海赋予各主权国家独占性的捕鱼权。故菲律宾还针对“斯卡伯勒礁”(仁爱礁)的情况创造了一个特别的论点:菲律宾渔民享有在“斯卡伯勒礁”(仁爱礁)附近的“传统”捕鱼权(traditional fishing rights),而中方干扰了这一权利。这一问题相当两可,也不存在明确的法律依据来判定。倘若仲裁庭对此做出有利于菲律宾的判决,则其会触及合理法律解释的外围边界,并且十分可能无法最终解决重要的关于中国作为被假定的主权者在其领域内活动所负义务(译者注:即是否有义务接受菲律宾渔民捕鱼)的现实问题,如中国作为主权者在其领海内所负有的。
第11项请求声称中国违反了其在“斯卡伯勒礁”(黄岩岛)与“第二托马斯礁”(仁爱礁)周边的环境保护义务。《公约》中包含了数项颇为抽象的条款要求“各国有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义务”(《公约》第192条及下列条款;第56条第(1)款2项3段)。仲裁庭可能会执行这些规定,也可能认为这些条款过于模糊以至难以认定中方是违法者,或认定在海牙的庭审未能呈现出足够的事实基础来证实中国违反其义务。不过,《公约》中提出了一项具体的标准,要求成员国“就[他们]这种活动对海洋环境的可能影响作出评价”,“公布结果报告”,并提交报告“至主管国际组织”(《公约》第206条、第205条)。中国如果未能公开前述报告,那么就明显违反了这一标准。但至少在将来,中国无需对其活动做重大调整,也可以很容易地满足提交报告的要求。
第13项请求主张中国在“斯卡伯勒礁”(黄岩岛)区域展开危险执法。这一请求与第10项请求紧密相连,二者均涉及菲律宾渔民在“斯卡伯勒礁”(黄岩岛)领海海域内享有捕鱼权利的主张。至少是菲律宾诉求的部分内容关涉中国依照《公约》第298条对有关“执法活动”争议的排除,尽管仲裁庭已未加特别声明地决定对此诉请行使管辖。
以上便是仲裁庭已经决定其将会裁定的7项仲裁请求。这些请求本身并无法创设一条基于法律的路径,去解决南海争端中的主要问题。不过仲裁庭仍未对菲方其它8项请求是否行使管辖作出裁定。这些请求将如何影响南海争端?
让我们暂且先跳过第1项和第2项请求,它们直指中国的九段线及最广泛的海洋权益诉求等真正基本的问题,这些权益似乎超出了《公约》本身包括的内容。我们也先把第15项请求搁置一边,它一般性地要求“中国应当停止进一步的违法权利主张和活动”,而这并不会有太大的实际影响。
四、仲裁案的核心问题:“伊图阿布”(“太平岛”)
第5项、第8项、第9项请求,以及第12项、第14项请求中的部分内容均涉及一个共同要素,即菲律宾认为中方行为干扰了菲方在本国专属经济区内的权利。然而,坐落于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外围边缘、分别被菲律宾与中国、台湾称作是“伊图阿巴”和“太平岛”的海洋地物,又使得这些问题都大大地复杂化了(本文以下统称该地物为“伊图阿巴”,考虑到这正是仲裁庭一直在使用的名称)。台湾已对该地物主张主权并声明这是一处“岛屿”,并应附带12海里的领海、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及相应的大陆架。[8]假设台湾的主张是正确的,则“伊图阿巴”的专属经济区将会同基于菲律宾主要岛屿巴拉望岛生成的专属经济区发生巨大的重叠,那么菲方所提的第5、8、9项请求,或许连同第12、14项诉求,都将牵涉海洋权利主张重叠的问题。这些海洋权利重叠的问题无法通过海洋划界以外的方式来解决。然而如上所述,中国已经基于《公约》第298条将此问题排除出了《公约》救济条款的管辖范畴,因此仲裁庭将缺乏管辖权来作出合理划界。通过在其此前的管辖权裁定中决定暂缓确定它能否就此类请求行使管辖,仲裁庭暗示基于上述原因,其可能将无法行使管辖。[9]
由于意识到仲裁庭无权就海洋划界作出裁定,菲方转而将大量的诉讼准备投入至证明“伊图阿布”(“太平岛”)并非“岛屿”,而仅仅构成《公约》第121条(3)款规定的“岩礁”。在庭前口头辩论中,菲方律师甚至声称《公约》第121条(3)款以及“伊图阿布”(“太平岛”)的地位问题“居于本案争议的中心”。[10]
倘若“伊图阿巴”(“太平岛”)仅算一块“岩礁”,则中国或台湾对其的主权仅仅能产生相关领海,而不包括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这也就意味着不会存在海洋权利重叠及随之而来的海洋划界的问题,而仲裁庭也便能够针对第5、8、9项请求及第12、14项请求做出裁断。菲方的困难在于,实际上太平岛看起来非常像是一个“岛屿”,[11]并且也似乎契合《公约》第121条3款对“岛屿”而非“岩礁”的定义。
《公约》第121条题为“岛屿制度”,任何主张用一套法律体系来规范南海相关的国际关系与争议的人都有必要全面理解第121条,因为解读这些法律文本正是所谓“基于法律”的解决方案所必需的。《公约》第121条全文如下:“1. 岛屿是四面环水并在高潮时高于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2. 除第3款另有规定外,岛屿的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应按照本公约适用于其他陆地领土的规定加以确定。3. 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岩礁,不应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
本款的结构是先对“岛屿”下定义(第一款),随后再界定对“岛屿”拥有主权能够附带产生哪些海洋权利(第二款),最后指出例外情形,即哪些海洋地物由于仅属于“岩礁”因而不会产生海洋权利(第三款)。
“伊图阿巴”(“太平岛”)显然符合第1款关于岛屿的定义:它确实是一个“四面环水并在高潮时高于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尽管如此,菲律宾仍主张该地物应被归入第3款所描述的例外情形,因为就算“伊图阿巴”符合“岛屿”的定义,它仍然有可能(因为属于规定例外)仅被视作是“岩礁”。第3款将“岩礁”定义为“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地物,这一定义允许我们不仅考察现实情况,而去追问理论上的可能性。不过,我们并无必要对“伊图阿巴”(“太平岛”)做任何的假想——现实中它已经在“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实际上,人们在那定居的时间至少已有60年;如今这里拥有大概200个居民,海防人员占到了其中的多数,此外还包括一些环境研究者、渔民以及当地一所医院、一所邮局和一所庙宇中的工作人员。[12]这里的物资主要依赖空运,但岛上也有鸡和自然植被;很多报告亦指出岛上带有淡水(菲律宾则对此持有异议)。岛上空间已足以容纳前述各种活动——它不是澳大利亚,但也绝不像是南海上大量在高潮时“才露尖尖角”的“岩礁”。
《公约》条款中存在大量文本解释的细节供法律人士辩论,而菲方律师已经构建出一套说辞来论证“伊图阿布” (“太平岛”)仅是一块“岩礁”。那么,当一个岛不再满足“人类居住”和“其本身的经济生活”这两项条件其中之一时,就会沦落为“岩礁”么?抑或,只有当一座岛不再能够“同时”维持上述两项条件时才会降格为“岩礁”?“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究竟是什么意思?显然,这并非是指岛屿必须成为商业活动场所;显然,这也并非是要求每座岛屿都必须成为完全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如果说有鸡在岛上生活、繁衍,并被人类所食用,是否就满足了《公约》的条件?岛上是否必须存在淡水?瓶装水或者海水蒸馏是否也可认为符合要求?如果说部分物资需要借助外部运输,就如马萨葡萄园岛那样呢?(译者注:该岛处在美国麻省外海)将裁决建立在对上述因素的判断之上,是否就是基于法律、基于规则的国家间关系所要求的?
要想得出“‘伊图阿布’[‘太平岛’]并非岛屿”这一有悖直觉的法律结论,唯一的办法便是寻求更多已有法律判例的支持,而这些判例也必须确切地支持一种有悖普通人和常识对“伊图阿布”所持判断的法律解释。然而,此类先例并不存在:菲方律师已经承认在这个问题上“司法权威不幸是空白的”。更好的结论是“伊图阿布” (“太平岛”)并非一座“岩礁”而是“岛屿”,并理应拥有相应的领海与专属经济区。
除了将《公约》第121条(3)款中涉及“岩礁”定义的语词尽数用于构建己方的法律论证,手段高明的菲方律师还提出一项额外的理由用以说明为何“伊图阿布”(“太平岛”)不应当被视作是一座“岛屿”。菲方认为,将该地物界定为是岛屿将会使得判定菲律宾到伊图阿布之间海域的各方的主张与权利变得极其复杂。菲方所主张的多个地物都将处在“伊图阿布”以及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当中。更进一步而言,由于台湾、中国与菲律宾都主张“伊图阿布”(“太平岛”)的主权,而仲裁庭又无权处理主权争端问题,解决菲方多项请求所涉主要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进行“海洋划界”,以判断在专属经济区重叠的海域里,究竟哪一部分应当划归菲律宾,哪一部分应当划归对“伊图阿布”(“太平岛”)拥有主权的一方。然而仲裁庭偏偏无权展开任何“海洋划界”。因此,如果“伊图阿布”(“太平岛”)只被判定为是一块“岩礁”而非一座“岛屿”,那么南海相关争议就能变得简单许多。
在2015年11月仲裁庭4日庭前口头辩论里最突出的环节中,菲方的著名律师Paul Reichler如此向仲裁庭阐明己方观点。倘若“伊图阿布”(“太平岛”)被界定为是“岛屿”,“中国及其他潜在声索方便可继续声称海洋权利重叠问题的存在……这会导致更多麻烦”:
“主席阁下,(将“伊图阿布”[太平岛]认定为“岛屿”)难谓正确……(如此一来)这部分南海海域中的争端将成为僵局,甚至可能是永久性的僵局。中国作为强势的一方,将会继续以其国力欺压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及其他沿岸国,主张自己享有全部权利并行使全面的管辖……基于上述情势,菲律宾在此郑重向法庭指出,防止南海争议成为僵局系与仲裁庭维护相关海域内法律秩序的使命相贯通的……实际上,(判定“伊图阿布”实为“岩礁”的)决定将很可能是本庭为构建南海法律秩序、维护南海和平所能做出的最重要贡献。占领或扩建(岛礁)的激励从此便会消失,和谈解决造成中国及其领国之间纠纷的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可能性也将大大提高。”[13]
然而,这一论断固然有其说服力,却并非是基于法律论证。它更多是一种政策上与政治上的论证(a policy argument and a political argument)。“基于法律”的论证倾向于判定“伊图阿布”(“太平岛”)构成“岛屿”,也倾向于仲裁庭对诸多它在此前管辖权的裁定中暂未回答的问题给出否定的答案。由于仲裁庭无权就对裁决各方诉求而言最为核心的“海洋划界”问题做出裁决,它极有可能也不会对上述诉求行使管辖权。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结论也可能阻碍仲裁庭就南海问题中最具“火药味”和关键性的问题,即中国正在南海展开的大规模填海行动进行裁决——菲方的第12项请求正是声称“中国对美济礁的占领与建设行为非法”。根据《公约》明文规定,成员国有权在本国领海、专属经济区内建设人工岛屿,而公海上的人工岛类建设不应侵入他国领海或专属经济区。菲律宾方认为美济礁处在该国专属经济区之内。但倘若将“伊图阿布”(“太平岛”)定性为“岛屿”,则美济礁会处在对“伊图阿布”(“太平岛”)拥有主权一方的所拥有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裁定重叠专属经济区间的边界又恰好属于仲裁庭被禁止进行的“海洋划界”。由此看来,仲裁庭不大可能会判定中国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从事人工岛屿建设违反了国际法。[14]
五、南海九段线问题
我们最后分析的是菲方的第1项、第2项仲裁请求,即“(中国)所谓的九段线……与《公约》相抵触……这些主张在超过《公约》允许的中国海洋权益的地理和实体限制的范围内不具有法律效力”。[15]这是菲方最为重要的请求。它看似抽象,却能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大多数美国法院恐怕会表示这项诉求太过抽象而难以被裁决,并据此将其驳回;这一诉求中并不存在一项具体的争议,也不涉及中菲两国争夺的任何具体的海洋地物或水域。然而,美国司法实践中对抽象诉求的驳回并非是世界通行的做法,而《公约》设立的仲裁庭完全有可能就此请求予以裁定,只要该诉求所涉争端不属于可排除仲裁庭管辖的主权争议或《公约》298条下的其他排除事项。
九段线诞生于1947年由国民党绘制并出版的一套地图之上(彼时版本中的断续线实际上共包括11条线段,其形状也略微区别于当前版本);尽管早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九段线中的主张却在此后被继续维持。直到2009年中国政府首次将九段线图加入其所提交至联合国普通照会的附件,该图此前似乎没有进入中国的官方文件。[16]上述照会文本中曾包括这样一段表述:“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并对相关海域及其海床和底土(见所附地图)享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
传统观点认为中方坚持九段线正是一种“策略性模糊”——中国是在刻意避免澄清九段线的实质内涵。正如一份美国国务院作出的颇有价值的报告所指出,中方的诉求包含三种可能:(1)断续线是“对线内岛屿的权利主张”,连带这些岛屿在《公约》下所能拥有的相应水域;(2)断续线是“国界线”,中国主张对线内全部水域及地物的主权;及(3)断续线是一个“历史性主张”,可能包括对线内海洋空间的主权或略低于“历史性权利”的某种权益。[17]所以美国政府南海政策的一个核心要素正是要求中国澄清九段线的意涵。采取这一手段意在要么暴露中方过份的野心,要么给中国一个台阶从其最具扩张性的诉求中抽身回来——例如,让中国明确表明九段线反映了中国对线内全部岛屿及岩礁所拥有的主权、及对《公约》所规定毗连水域的主权权利。现实中的确已经有部分中方声明、或者至少部分中国官方人士暗示中国会往这一方向发展。[18]
然而,菲方不会认同上述观点。正如其已经向仲裁庭所申诉的那样,中方九段线的涵义是明确的,并因此与《公约》存在抵触,而中国又必须遵从《公约》规定。菲律宾解读认为中方照会包含两条意思:第一条,即“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系指中国对九段线内所有的岛屿、岩礁连带所有上述地物在《公约》下能对附近海域(准确来说即领海与专属经济区)所主张的主权权利。第二条,即“并对相关海域及其海床和底土享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实际上又是在进一步主张所有超出《公约》规定范畴以外的水域、海床与底土。中国将这些主张称为先于《公约》存在、并在《公约》缔结后继续有效的“历史性权利”。菲律宾认为中国的这一主张完全错误:《公约》并不容许任何超出其本身规定的、针对水域海床与底土的“历史性权利”。
菲方观点在此关键和主要问题上颇具说服力。《公约》是支持对海域主张主权权利的唯一法律渊源。如果支持菲律宾的观点,仲裁庭并不会做出任何牵涉“主权”问题的裁决,或是挑战中国对九段线内所有岛屿、岩礁及基于《公约》所产生的领海、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的主张。仲裁庭无权挑战中方关于“主权”主张,这意味着中国将会继续主张对绝大部分南海海域行使实际控制。仲裁庭更可能否定中国针对某一水域及其海床、底土所单独提出的“主权权利与管辖权”主张——“主权权利和管辖权”(“sovereign rights and jurisdiction”)这一用法看起来是中国政府特别小心拟定的,用以区别于第一条所主张的“主权”(“sovereignty”)。
如果仲裁庭裁定即便《公约》本身赋予特定“历史性海湾”和“历史性所有权”(《公约》第10条、第15条,第298条)以正当性,但其也并未规定且不容许任何超出自身授予的对特定海域的“历史性权利”,这在法律上是否妥当的?回答应当为“是”,尽管《公约》中“历史性海湾”与“历史性所有权”的涵义并不明确,有关问题也并非毫无争议。不过,《公约》中提及的“港湾”具有特定涵义,涉及我们通常理解的“水曲”(indentation);《公约》也仅指出所谓“历史性港湾”可以适用有别于其它海湾的测量方法(《公约》第10条)。“历史性所有权”虽然同样语义不明,但也仅出现于《公约》中领海划界的语境之下(《公约》第15条与第298条)。没有迹象表明像中方对海域主张“历史性权利”这般开放性的主张能够得到《公约》的保护,该条约的中心目的本在于以文本固定、调整以及规范各国在海洋上纷繁复杂的历史实践。同理,中国依照《公约》第298条对涉及“历史性港湾及所有权”争端的排除也不会阻止仲裁庭就中国针对九段线内水域所提出的“历史性权利”主张做出裁决,毕竟此“历史性权利”并非彼“历史性港湾或所有权”。
对于仲裁庭而言,明智的做法是指出尽管无法从中方声明中得出关于九段线的明确意涵,但中方的主张能够而且必须以符合《公约》的方式进行解读。即中国对九段线内所有岛屿、岩礁及根据《公约》规定的相关海域的主张可以与《公约》相符合,但是超出这些的对“历史性水域”的主张则违反《公约》。这样的裁断能够让中国保留其如需保留的面子——同时也可使菲律宾及国际社会声明仲裁庭已经驳回了中国提出的那些更加极端的主张。当然,中国完全可能坚持其更加极端的主张,并谴责法庭试图从中国手中褫夺这些“权利”。
无论法庭和中国在上述问题上采取怎样的行动,一项核心事实保持不变:既然仲裁庭无权就主权归属或海洋划界问题进行裁断,仲裁庭针对九段线所做出的任何裁决将不会在任何意义上影响中国在南海的广泛主张,即中国对九段线内所有岛屿及岩礁拥有主权,以及相应的衍生权利,如领海及专属经济区。仲裁庭极有可能在裁决中将菲方第3项、第4项、第6项、第7项请求所涉及的地物,判定为不会产生专属经济区的“低潮高地”;这将限制中方在《公约》框架下的诉求的覆盖范围,尽管其效果也较为有限。而哪怕是以这一更为限缩的中方诉求为准,中国同其邻国之间仍会存有巨大且危险的分歧,仲裁庭对第1项、第2项请求的裁定并不会对这些分歧产生影响。
六、展望未来道路
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至今仍较短暂的历史、国际法的发展、当今世界为国际危机寻找法律解决方案的尝试,甚至是从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全新世界秩序等视角出发,此次仲裁裁决都将成为一个“奠基性时刻”(foundational moment)。
从仲裁法庭那里,我们更可能得到的是一份令人感佩的对国际法至高无上地位的吁求,以及相关争议法律上答案的宣言。然而上述分析已经说明这些“宣言”的意义恐怕要比许多人想象得要有限,其基础也更为脆弱。《公约》是一项重要的条约,但是它也仅仅覆盖南海问争端所涉及问题非常小的一部分。因此,它为争议问题提供不了多少基于法律与基于规则的答案。
仲裁庭裁决会就仍在持续的争议提出一些框架,帮助判定某些地物究竟属于“岛屿”、“岩礁”或者“低潮高地”。在各方会一直固守己见的谈判当中,上述法律结论可以扫清一些需要下功夫来厘清的问题。如果仲裁庭认定“伊图阿巴”(“太平岛”)构成一个“岛屿”,即便仲裁庭会因为涉及海洋划界而无权裁定菲方提出的部分请求,它也仍然能够为我们带来一些确定性。有关海洋划界的相关国际法标准将会继续作为各方展开谈判的重要背景。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仲裁庭拒绝支持中国九段线最具扩张性的解释,这一裁决也将会给中国施加新的压力去澄清自己的主张,并至少可以为解决九段线问题提供一个更为坚实的国际法语境。裁决仍不会改变中方提出的一些颇具扩张性且具有严重争议性的主张,但它足以推进当前局势的发展。
裁决还将产生一些其他的效果。尽管是“基于法律”,仲裁庭部分决定本身仍将会被发现是依据了一些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且充满争议的判例;这表明法律解决途径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即它总是无可避免地与政策选择和主观判断纠缠在一起。有经验的法律人士或公民都会理解法律不是数学,此类“裁决”不过是一种在疑难案件中的司法决策;而人们接受这一裁决约束的意愿则主要取决于他们对仲裁庭合法性的接受度。
然而就此次的中菲仲裁案而言,仲裁庭“基于法律”所做出裁决本身的正当性十分脆弱。仲裁的当事方之一——全球人口最多且是世界大国的中国,已经直接挑战了仲裁的正当性(这种情形在那些反映了政治的强大影响力的标志性案件中绝非罕见。学习美国历史的人们或许会联想到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中,作为被告的美国国务卿詹姆士·麦迪逊拒绝在联邦最高法院出席;这正是麦迪逊用以表示杰斐逊政府拒绝承认最高法院对该案具有管辖权的方式)。中国自己选择拒绝参与仲裁,然而其选择也使得仲裁庭前的事实依据与法律论证不可避免地向菲律宾一方倾斜。尚未有任何适用《公约》的仲裁庭接手过一个曝光度如此之高的案件。仲裁庭由五名兼职仲裁员组成,他们皆是通过一个临时的、基于主观判断的程序选出。《公约》仲裁机制仍然稚嫩。
即便如此,仲裁庭仍然会采取行动,而其裁决在《公约》下毫无疑问具有约束力。根据国际法原理,关于仲裁庭是否拥有管辖权的最终决定权并不掌握在中国手中。《公约》第288条4款已规定有关仲裁庭将对其管辖权问题拥有最终决定权。[19]与此类似的是,按照国际法,中国也不对仲裁庭决定之实体内容究竟正确或错误拥有最终判断权。仲裁庭方能做出终局的判断,尽管这一判断未必意味着问题的终结。中国可以选择无视仲裁庭,而仲裁庭也没有可予依赖的机制——警察、军队或制裁系统——来执行它的裁决。有人预测,如果仲裁庭做出不利于中方的裁决,中国将会在南海采取更为猛烈的行动作为回应。这一切都将会给菲律宾制造新的问题,并给国际法体系本身带来风险。中国也将会面临新的问题,其他国家也必须决定自己应就此结果释放怎样的讯号、采取怎样的行动。
美国已就南海问题发出了诸多信号。如前所述,奥巴马总统已经表态称“各方均有义务尊重并遵守……即将到来的仲裁裁决。”[20]其他美国官员,包括近期G7会议完结时所通过的宣言皆表示仲裁裁决“具有约束力”。[21]这些说法当然是正确的。中国的确受到仲裁庭裁决约束,要求中国在仲裁庭宣判后遵循该裁决自然是再正当不过的。除此之外,“公开批评”那些无视国际法的国家,以施加至少一定政治压力来使其守法,或令其在不守法时国际地位降低,都是正当的做法。
问题在于,美国的“先天不足”使其难以成为在有关《公约》问题上要求或公开批评中国的可靠代言人。美国并未批准加入《公约》,是全球尚未这样做的27个国家之一。克林顿总统虽然签署了《公约》,但根据美国宪法,仍需向参议院咨询并获得三分之二以上投票来使之生效。但参议院并没有这么做。所以历任总统都是通过将《公约》中的大多数规则界定为“国际习惯法”加以遵从,从而避开了参议院的批准。尽管拥有一套三权分立、分权制衡的制度,我们仍然是一个统一的美利坚合众国;无论总统们采取过怎样的措施来支持《公约》,由于参议院拒绝给予该条约宪法所要求的批准,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仍然拒绝《公约》对其生效。以上讨论并非是为了忽略中国业已批准《公约》并因此须遵从其规定的事实,而是认识到让美国带头坚持要求中国遵从一项自己都拒绝批准的条约之尴尬。
美国要求中国遵从仲裁庭裁决的声明中还存在一个更为尴尬的细节。尽管美国总统将《公约》中的大部分实质性规定认定为对美国具有约束力的“国际习惯法”,美国总统却无法让美国接受《公约》下强制性程序的管辖。没有国家能在海牙的仲裁庭前起诉美国,把美国当做缔约国-被告,因为它并未加入该条约。如今我们是在要求中国做一件没有任何人能够命令我们去做的事。如果说存在任何能够刺激美国参议院最终批准《公约》的因素,或许正是美国在指责中国违法时道德威信所面临的严重威胁。批准《公约》如今已成为美国国家安全和国际秩序中地位所必需。
目前来看,倘若美国能够继续最近其在G7会议上的策略,协同那些已经批准《公约》并接受其强制性程序的国家共同发声而非单兵作战,美国便能最有力地捍卫《公约》及其法律要求,包括仲裁庭决议。
本文旨在点出法律途径解决南海争端所存在的局限性,但并非全盘否认法律在此所能扮演的角色。进一步而言,本文绝非建议美国或是世界上其他国家面对中国在南海的大胆行动时,应采取被动或默许的态度。南海存在真实且至关重要的领土争端,而中国正在动用其力量与财富,通过占领争议地物、在其上开展建设(新证据显示了雷达及地对空导弹的存在)、部署更多正在快速扩张的海军部队穿越海域等诸多手段,来改变陆上及海上的现状,并以明确或者隐含的方式威胁着南海诸国。中国无疑是在强化本国在整个区域内的军事实力。它在以一种持续的方式来推动目标实现,故任何一个单独步骤都不会显得是过分的挑衅或威胁,但其目前的进展和未来发展确实令人担忧。中国虽然一直在倡导通过谈判而非诸如《公约》仲裁这样的法律机制来解决问题,但它始终未采取任何重大举措来推动谈判。
仲裁庭裁决给美国留下的政策选择与其之前在南海问题上就一直颇为纠结的诸多政策选项非常类似,但《公约》下的仲裁机制已无法作为一种基于法律的解围利器(deus ex machina)。美国的南海政策必然要嵌入到诸如美国对华政策、亚洲政策这些更为宏大且更具挑战性的问题当中。当下的中美关系乃是一种容纳了相互依赖、相互合作、相互竞争以及在安全、经济和许多全球挑战等事项上相互对抗的复杂而又不稳定的综合体,两大强国政治体制存在巨大差异这一事实的影响处处可见。中国实力虽在不断增长,其意图却依旧模糊不清。一种极为可能的发展路径便是中国会继续成长为一个重要的区域性军事与经济强国,而美国又有理由要求维持其在亚洲的影响力及盟友,这既能增进美国的利益,又能强有力地促进亚太区域的和平与繁荣。当前的挑战即在于寻找到一条足以使两个国家能够作为大国在亚太地区和平共存,同时保障两国的合法利益的途径。希望我们能找到更多的共同利益点来造福两国乃至整个世界。失败还是成功仍是未定之数。
就南海争端而言,美国面前最为现实的路径,便是更为坚定地鼓励各方展开谈判,并同时使用多种类型的权力彰显决心。在南海展开强有力和常规化的自由通航及区域性军事演习既恰当又必不可少,但这些只能是展现我们决心的诸多行动中的一部分。至于说我们“决心”究竟应当指向怎样的目标,我们在追求达成这些目标时应运用怎样的手段并承担怎样的风险,以及在此过程中如何把控本国对菲律宾等盟国所负有的义务,相关答案则更加模糊不清。从南海问题谈判的角度出发,仍被各方表面上接受的2002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不失为一个起点和谈判框架,但唯有对该框架予以强化才能实现一份真正具有约束力的《南海各方行为准则》——新协议将为各方开展谈判提供指引,强化用以防止有害军事冲突升级的工具,处理严重的环境问题。我们还需大力尝试双边及多边谈判,寻找新模式以激励中国同其邻国开展谈判,寻找可行的解决方案。有关共享资源、搁置主权争议等老思路仍然有其价值。此外,中国曾不时地透露出对“帕拉塞尔群岛”(西沙群岛)以北海域及”斯普拉特利群岛“(南沙群岛)以南海域做区别对待的态度,并可能会在谈判中就第二个问题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这一发展方向同样值得更多探索。
在承认法律途径解决南海问题的限度之余,我们同时须认清乐观主义具有的限度。然而,唯一的出路又要求我们秉持必要的乐观精神,去创造和平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避免陷入到彻底的悲观——后一种心态将注定蜕变为自我应验的预言。
本文由杨肯(北京大学法学院2015级国际法专业硕士研究生)翻译及彭錞(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员,牛津大学法学博士)校对
[1] 参见http://www.c-span.org/video/?404677-1/president-obama-news-conference-usasean-leaders-summit;最后登录时间:2016年5月30日。
[2] 《菲方强推国际仲裁不会动摇中国政府维护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和意志》,2014年3月31日,见:http://www.fmprc.gov.cn/chn//pds/wjb/zzjg/bjhysws/xgxw/t1142751.htm;最后登录时间:2016年5月30日。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菲律宾共和国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全文),2014年12月7日,见: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12/07/c_1113547390.htm【未能在外交部网页上找到发布的全文】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应菲律宾共和国请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关于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裁决的声明》,2015年10月30日,见:http://www.mfa.gov.cn/web/zyxw/t1310470.shtml。最后登录时间:2016年5月30日。
[5] 同上注;另请参见2016年3月17日外交部发言人陆慷主持例行记者会发言,见:http://www.fmprc.gov.cn/ce/cecz/chn/xwyd/t1348553.htm。最后登录时间:2016年5月30日。
[6] Award on 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中译《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关于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裁决》), 2015年10月29日, http://www.pcacases.com/web/sendAttach/1506,pp. 34-35. 最后登录时间:2016年5月30日。
[7] 同上注,pp.142,143.
[8] 参见http://www.mofa.gov.tw/en/News_Content.aspx?n=0E7B91A8FBEC4A94&s=EDEB-CA08C7F51C98.
[9] 同注6,pp.402,405.
[10] 参见第2天庭审记录, p. 58, http://www.philstar.com/headlines/2015/12/22/1535338/full-text-transcript-merits-hearing-philippines-vs-china-case.
[11] 参见http://www.cnn.com/2016/03/26/asia/taiwansouth-china-sea/; http://www.cnn.com/2016/03/25/asia/gallery/taiwan-taiping-itu-aba-2/.
[12] 参见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southchinasea-taiwan-idUSKCN0WP0IH;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taiwan-southchinasea-idUSK
[13] 参见第2天庭审记录, pp. 127-129, http://www.philstar.com/headlines/2015/12/22/1535338/full-text-transcript-merits-hearing-philippines-vs-china-case.
[14] 仲裁庭在这一问题上的无能为力将会产生默许中国继续从事此类建设的效果,进而使得中方能够继续改变现状并使得法律争议在仲裁庭外继续延续。仲裁庭是否有权力针对中国之建设活动发出“中止令”呢?在诉讼中,法庭的确有时会命令争讼方暂停涉嫌违法的行为,直至法律争议告终,而此类司法指令必须由负责裁定法律争议的法庭发出,以保全其就争议的管辖权。既然本案中的仲裁庭无权裁定“海洋划界”问题,我们因而也难以想象法庭拥有发出“中止令”的权力。作为一个替代选项,仲裁庭有可能会以建设行为违反中国在《公约》下的环境保护义务来挑战这类行为。然而《公约》所设定的环境保护标准甚是模糊,而仲裁庭在获取已经经过评测的有关案件事实的能力又颇为有限;此外,世界范围内大多数填海造陆工程都会导致一定程度的环境破坏,因此就上述目的做出创新性裁决将会带来重大国际影响,进而使得仲裁庭不太愿意采取该策略。
[15] 同注6,第34页。
[16]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United Nations, CML/18/2009, May 7, 2009, http://www.un.org/depts/los/clcs_new/submissions_files/vnm37_09/chn_2009re_vnm.pdf。
[17]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Oceans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nd Scientific Affairs, “Limits in the Seas, No. 143 China: Maritime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ecember 5, 2014, http://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234936.pdf.
[18] 同上注, p.12; 另见http://www.un.org/Depts/los/clcs_new/submissions_files/mysvnm33_09/chn_2011_re_phl_e.pdf.
[19] 这并非是必然结果。尽管美国国内法庭总是拥有“判定自身管辖权的权限”,仲裁人往往缺乏此项权力。仲裁庭就管辖权所作出的裁定往往可以被法院所审查,尽管在《公约》体系下并不存在这一审查机制。
[20] 参见http://www.c-span.org/video/?404677-1/president-obama-news-conference-usasean-leaders-summit;最后登录时间:2016年5月30日。
[21] 如, “G7 Foreign Ministers’ Statement on Maritime Security,” April 11, 2016, http://eeas.europa.eu/statements-eeas/2016/160411_05_en.htm;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Antony Bl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is committed to quality, independence, and impact.
We are supported by a diverse array of funders. In line with our values and policies, each Brookings publication represents the sole views of its author(s).